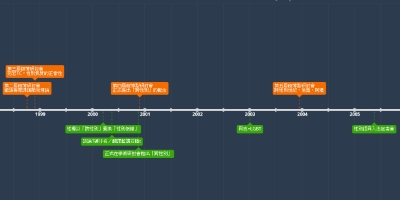2 dez 2000 ano - 兩性,跨階級、跨性別。
Descrição:
族群與民族認同 須獲承認與尊重【張茂桂╱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】
吳忻怡╱台大社會所博士生
這篇文章討論台灣所通稱的「省籍問題」,或者說「外省人」和「台灣人」之間,彼此看法相左的現象。所謂「相左看法」,不僅只是「觀點差異」、或者「史觀」不同的問題,還包括它們之間所具有的對立與激動性。不同的論者,可以對於「他者」,以及「他者」的觀點,感覺非常憤怒,予以嚴厲批判或者攻擊。而被論述者的反擊,也經常使用同樣激動,甚或升高激動的情緒。
而這樣的情緒,不止是台灣人在討論省籍問題、民族主義差異時可能發生。同樣,在討論台海兩岸的「統獨」走向時,不同立場的兩岸人民,都可能有激烈的語言與情緒,甚至到愛者欲其生,恨者欲其死的對立局面。連「民族戰爭」也可以考慮,既便是在學術研討會上亦然。
這篇短文,嘗試去討論這個容易讓人激動問題,並且將指出,所有關於「身份認同」的爭議,除了利益、工具目的之外,還有相互承認與尊嚴的問題。
「認同」和「尊嚴」的關係在哪裡呢?在於我們是否認識到「認同」不是簡單的政治口號運作,「認同」也不是「歸屬與否」的情感問題;而是在我們是否認識到「認同」是關於個人的◆事如何和集體的◆事,取得某種程度的連結與共構,以及是否能取得相互的支持與道德力量。當我們用國家權力,用論述,否定他者的認同,侵犯他者的道德識域,將創造出羞辱的情境,而進一步引發緊張或者衝突的族群關係。當然,強調「認同與尊嚴」,並不是意圖去否定所有關於階級利益與政客的工具性操作,而是假定社會上若沒有台灣人的不平等的切身感受,或者假定沒有外省人的受辱感覺,那所有的政治操控技術,不會達到單方面的效果。
台灣人意識的來源有多重歷史面向,不同的歷史作用力,不同的歷史情境壓力,好像在黏土上刻畫下不同的痕跡。從一九四五年之後,因為高文化教化,以及語言的關係,讓我們對於台灣人意識的興起,和台灣人的集體尊嚴,特別是跨階級、跨性別的個人◆事的集體關連性,有更清楚的認識。而這樣的集體◆事故事,對一些外省人來說,是難以理解的。
反過來說,從一九八◆年代後期以來,在台灣外省人的道德識域與認同世界,所受到的衝擊,絕不小於他們在政治力量上的被邊緣化,外省人的所謂「危機感」,並沒有被正確的看待。民主的價值,比如「政黨輪替」,不會輕易取代個人◆事和集體◆事的共搭,也就產生了身份認同的問題,尤其,如果民主化是用教訓外省人過去的集體政治錯誤,和高文化的關連性,來進行的時候。我們可以說,一般台灣人對於外省人的論述,基本上缺乏承認與尊重,(但是卻也很難說是一種「妒恨心理」)。
認同不是單純的「我是誰」的問題,同時是個人的道德識域的問題,認同的道德識域,提供我們關於自身,以及關於他者的相對意義與看法。人們因為這樣的識域,而使得生活獲得意義。政治上的族群或民族認同,因此必須被尊重與承認。
最後,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台灣內部的省籍問題以及民族主義論述為主,但是,如本文在一開始時說道,這一個問題,有其普遍性。在討論兩岸關係時,不同的民族主義主張、不同光譜的統獨立場,仍然有它可能的意義。因為同樣是中華民族,但是兩岸分隔百年後的「認同」差異,兩岸都必須承認尊重,不但應認真檢視冷戰時期所遺留至今的刻板與對立的道德論述,也必須認真檢視兩岸因為政治制度、經濟水平的差異而發展的「優越論述」,就是優於對方的論述。而承認與尊重,也必須被整合到兩岸的政治談判之中,並且從根本上排除關於戰爭威脅的可能。如同泰勒指出,一旦發生戰爭,所有的「共善」基礎都不存在,不同族群或民族的群體,將非常困難尋求到道德上的接著點。戰爭的毀滅力量與社會動員將使認同與尊嚴的討論,無從進行。武裝衝突將在人們的生命◆事、集體的生活◆事所交織的黏土上,印下巨大而深刻的痕跡。(本文為東吳大學與民族主義學會合辦,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贊助「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反省」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)
【2000-12-02/聯合報/15版/民意論壇】
Adicionado na linha do tempo:
Data:
2 dez 2000 ano
Agora
~ 24 years ago